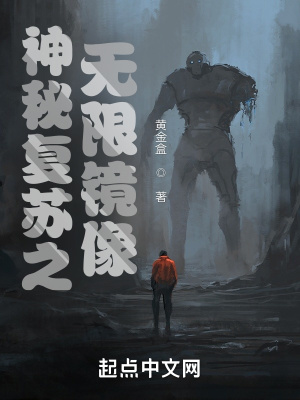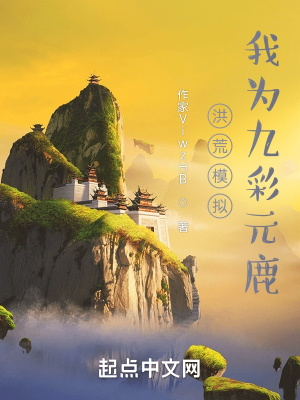久久书库>代晋 > 第一三八四章 进退二合一(第3页)
第一三八四章 进退二合一(第3页)
但是,另一方面,京口如此迅速的被攻下,给了桓玄极大的震慑。听了桓伟的禀报之后,桓玄更是心中胆寒。若说之前,桓玄还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和东府军一分高下的话,眼下桓玄则毫无信心了。
京口被攻下了,门户已失。水军遭受重创,已经难以封锁大江,无法阻止东府军增兵。而东府军在京口水战和攻城战中展现的雷霆之势着实令人胆寒。桓玄对战胜李徽已经失去了信心。虽然桓嗣在得知桓谦死后立刻要求率军进攻京口,但正是因为担心不敌,造成更坏的结果,桓玄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今日桓玄之所以要召集朝会商议此事,其实便是他焦虑和信心不足的表现。他希望朝廷将李徽打成反叛,这样便可绑架上下一起对付李徽,而将这件本来是私人的恩怨上升到国家层面。这其实也是一种弥补的方式。
眼下的情形,桓玄不得不多做一番考虑。今日陛下说的这番话明显是有人在背后指使。以司马德宗的智慧,当说不出这番话来。这说明朝中可不是铁板一块,有人已经开始抱团反对自己,通过司马德宗来牵制自己。
而桓玄其实最怕的便是,此时此刻若是李徽亮明态度,就像当初的王恭和不久前的自己一样,打出靖难的旗号,将矛头指向自己。那么事情便将变得极为麻烦。自己会遭受朝廷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到那时真的是一点余地也没有了。
问题的关键便在于,所有人都知道此次李徽出兵的原因便是诱捕周澈的计划引起的。司马德宗也当众戳穿了此事,其实就是在告诫自己,这件事因自己而起。这时候李徽若是再来个针对自己的起兵檄文,岂非是立刻形成了内外的联动,让自己完全的陷入了被动之中了。
桓玄踌躇着。此时此刻,他多么希望有人能帮自己分析这件事该如何处置才是最佳的方案。可是,没有人能够给他好的建议。他不由得再一次的想起被自己一怒之下杀了的卞范之了。自己可太蠢了,居然听信了王绪的话,斩断了自己的左膀右臂。偏偏打碎牙齿和血吞,自己还不能承认自己的愚蠢。
“郡公,
遇到决断之事,切记住一个原则。那便是,永远不要将自己逼入绝境之中,要给自己留回旋余地。成大事者,不可急于一时,要久久为功,进退有度。有时候,退便是进,进反而是退。”
桓玄的脑海里想起了卞范之当年对自己说的话。当年自己并不明白这些道理,甚至觉得卞范之好为人师有些令人厌恶。但是现在,桓玄突然想起卞范之的话,心中顿有所悟。
此时此刻,强行为之,便是将自己逼入绝境之中。如能退后一步,便有另外一片天地。自己意气用事,诱捕周澈不成,却又不肯放了庾冰柔,所以导致眼前的局面。现在估计朝廷上下都认为是自己的错,所以才有人站在司马德宗身后和自己反着干,这一切都是不好的兆头。
与其如此,不如退后一步,将庾冰柔放了,或许便可解决这场内外的危机。
不过到了目前这种情形之下,李徽未必肯罢手。但他若是不肯罢手,那便要让他坐实反叛之名,让朝廷上下的杂音消除。
桓玄吁了口气,心中有了计较。
“陛下之言,臣觉得颇有道理。臣也是太愤怒了,所以考虑欠妥。既然如此,臣请陛下下旨斥责李徽,询问其用意。陛下说李徽未必有反意,那便问问他到底要干什么。倘若他当真无造反之意,便当将兵马退出京口,其余的事都可协商解决。倘若他根本无视陛下的旨意,便恰好说明李徽乃是反叛,到那时,朝廷上下便当同仇敌忾,伐灭反贼。陛下以为如何?”
桓玄终于再众人的目光下缓缓开口道。
此言一出,许多人微微松了口气,认为桓玄这是退让了一步了。
司马德宗也吁了口气,点头道:“桓卿此言,朕认为颇为合宜。朕即刻下旨质询李徽的行为,看其反应。若当真是反叛之行,则举国伐之,名正言顺。他要作乱,岂能容他得逞。但若他并无反叛之意,而是因为一些其他的事情,桓卿认为可以商谈,那自然最好不过。无论如何,化干戈为玉帛,总是美事。桓卿可不要到时候又不同意,那岂非令朕难堪。”
桓玄沉声道:“臣怎会出尔反尔,陛下适才说的诱捕周澈的事情,臣回去彻查。倘有此事,必将周澈的妻儿送还,严惩行事之人。陛下放心便是。”
司马德宗点头笑道:“甚好,朕心甚慰。”
许多人都对桓玄突然转变的态度感到惊讶。他们不明白桓玄为何会变得通情达理起来。这样的转变显得颇为突兀和奇怪。但无论如何,桓玄能有这样的态度,总好过大动干戈。如能止息纷争,天下便可太平。那也是许多人都希望看到的结果。
有的人自然洞悉了桓玄的想法。此乃以退为进之策。
球,踢到了李徽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