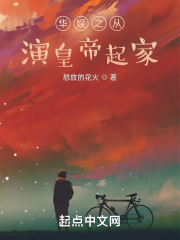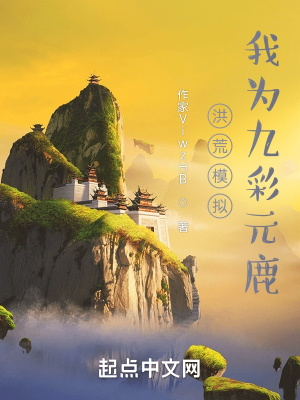久久书库>崇祯,师叔来教你做皇帝 > 第254章 不敢奉诏(第2页)
第254章 不敢奉诏(第2页)
“我根基不足,骤然升到那么高的位置,谁知道是祸是福。”韩庆之叹了口气,实话实说,“如果我能够选择,宁愿继续老老实实留在福州这边。山高皇帝远,外加海阔天空。”
“你果然这么说!”郑一官听得眼睛一亮,立刻笑着抚掌,“大学士派我出来来找你之前,就猜测,你未必愿意去登莱任职。朱巡抚也说,以你聪明,未必看不到其中危险。我还有些不信,没想到,真的被他们两个说中了。”
“朱巡抚知我!”韩庆之笑了笑,脸上的表情越发凝重。
“我其实知道的也不多,大部分消息,都是朱巡抚从南京那边带回来的,还有一些,则是道听途说。你托他做主,将战功给沿江各地官员分润,算是托对了人。在他的运作下,如今整个南京六部的大小官员,是个人都夸你懂得做事。”郑一官也收起了笑容,开始认真地介绍最近陆地上发生情况。“而他也凭着这些人脉,提前好几天,就得知了先皇的遗命,以及当今皇上的最终决定。”
这就是朱大典的本事了。全歼倭寇的战功,如果换了别人来向朝廷申报,未必能换回太多的好处。毕竟最近朝廷的关注重点在辽东。对倭寇之患,根本顾不上。
而把全歼倭寇的战功,从韩庆之一个人的头上,分给南京留守的和沿江各地的大小官员,众官员们就会一起努力,去从朝廷那边争取实惠。韩庆之凭借分剩下的那部分,反而比独占功劳收获更大。
此外,人脉这东西,在任何时代都不嫌多。南京六部官员,虽然都影响不了朝廷的决策,消息却极为灵通。他们承了朱大典和韩庆之的人情,北京那边有关二人的喜讯,当然会比朝廷的正式圣旨,更早一步传到朱大典耳朵里,以免他和韩庆之两人应对不及。
“据说,先皇在临终之前,回光返照,对很多事情都做出了安排。”看看四周围没有外人,郑一官压低了声音,继续介绍,“特别叮嘱当今圣上,启用孙承宗为首辅,重用九千岁魏忠贤。当今圣上即位之后,与朝臣们反复权衡,最终让孙承宗加了太师头衔,去辽东督师……”
他是海盗出身,言谈当中,不像其他官员那样,对皇帝和上司,都用各种尊称替代。当着韩庆之的面儿,更没有太多忌惮。所以,讲述起最近发生的情况来,反而更清楚明了。
在他的介绍下,韩庆之也终于知道了,自己出海这二十多天,大明朝究竟发生哪些大事,忍不住又在心里唏嘘不已。
木匠皇帝朱由校在缠绵病榻多年,终于在临终之前,脑子恢复了几分清醒。所以留下遗诏,安排孙承宗入阁为首辅,与魏忠贤一道辅佐自己的弟弟朱由检。并且对自己心目中的几个能臣,如太仆少卿杨鹤,贵州总督张鹤鸣等人,都做出了相应的安排。
然而,朱由检即位之后,内阁却以遗诏当中,很多安排是乱命,拒绝在圣旨上用印。朱由检本人,也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意接受这份遗诏。然而,毕竟皇位是从兄长那里继承的,张皇后的全力支持,对新皇帝朱由检来说也不可或缺。所以,几经勾兑之后,孙承宗就成了辽东督师,魏忠贤加了九锡,朝堂上也多了两个次辅,杨鹤与朱一冯。
至于贵州总督张鹤鸣,因为剿匪尚未结束,脱不开身,有关职位只能容后再议。
而所有安排当中,表面上看起来最为复杂的,就是韩庆之这边。因为有关他的任命,其实有两份。一份为天启皇帝去世之前发出的圣旨,任命他为天津总兵。另外一份,则是遗诏,任命他为登莱总兵。
天津总兵的重要性和权力大小,都远不如登莱总兵。对应的实际职位也只是山东都指挥使司同知,而不是山东都指挥使司副指挥使。
然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有关天津总兵这道圣旨,是魏忠贤的安排。至于登莱总兵,则完全是天启皇帝看到孙承宗送来的捷报之后,一时心血来潮。
所以,按照首辅韩旷的想法,这两个任命全都应该作废,理由是前后冲突,不知道究竟哪个,才是先帝的本意。
但是,已经把孙承宗从首辅位置,改成了辽东督师,再将对韩庆之遗命束之高阁,就对先帝有些太不尊重了。所以,最终,朝廷还是决定,以遗诏为主,让韩庆之捡了个大便宜,连升数级,以山东都指挥使司副指挥使的职位,出任登莱总兵!
“传旨的钦差到达福州之后,谁也找不到你。多亏朱巡抚肯花钱,才把钦差给留了下来,等你接旨。”将道听途说的消息,和朝廷的邸报结合起来,向韩庆之讲述完毕,郑一官笑着再次催促,“赶紧,升满帆,以最快速度返回福州。否则,钦差等不到你,可就带着圣旨返回北京了。”
他本以为,韩庆之会立刻下令全速赶赴福州,却不料,后者竟然果断将头转向身后一直默不做声的黄道周,郑重请教,“幼玄兄,我记得文官可以借口才疏学浅,拒绝奉诏。在大明,武将可以么?如果我拒绝出任登莱总兵,用什么理由最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