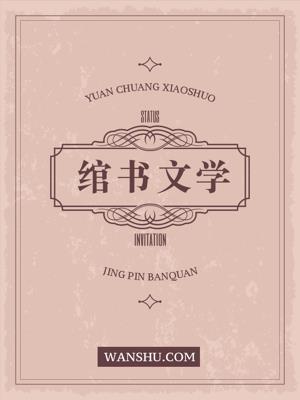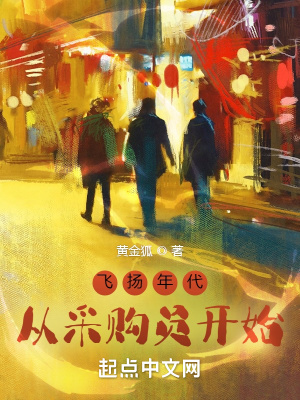久久书库>从德皇的司机开始征服世界 > 第1081章 法国现状(第1页)
第1081章 法国现状(第1页)
伊格纳季耶夫的座驾带着一股屈辱的尘烟,消失在东京戒备森严的街道尽头,那间外务省会议室内残留的冰冷与敌意象征着俄日之间最后一次基于绝望的媾和彻底化为了泡影。
两条在东亚泥潭中挣扎的受伤野兽,非但未能抱团取暖,反而在互相撕咬中耗尽了最后一点联合自保的微末可能。
谈判破裂的消息传回大本营,引发的并非反思,而是混合着愤怒与破罐破摔情绪的癫狂,在军部那些手握实权的将军们看来,俄国人的拒绝是“不识抬举”,是“腐朽白人贵族式的傲慢”。
他们宁愿将太平洋舰队这最后的资本葬送在冰冷的海参崴港内,也不愿将其交给“更有能力”的日本帝国使用,这本身就是对“八纮一宇”精神的亵渎。
“既然俄国佬自寻死路,那就让他们和支那人一起去死吧!”
陆军省军务局内,一名少壮派军官挥舞着拳头,面目狰狞地咆哮,然而,在这狂热的表象之下是难以掩饰的虚弱与恐惧。
局势已经明朗的只让人觉得残酷,俄国这只“路边野犬”的命运已无人关心,但日本帝国自身也早已是强弩之末。
在中国战场上,兵力、资源、士气都已濒临极限,德式装备武装起来的中国军队,在东北发起的反攻锐不可当,关东军节节败退,通往朝鲜半岛的退路正变得越来越狭窄。
海军在海上与德属东亚的消耗中也渐显疲态。
此刻对于日本而言,最理性、最能保存国体的选择无疑是立刻通过中立国渠道,向中德两国发出求和的信号,争取在尚且保有部分谈判筹码(如完整的本土、部分海军力量)时坐上谈判桌,哪怕付出巨大代价也能避免最可怕的结局——本土登陆战,帝国的彻底覆灭。
然而,“理性”在此时的东京已成奢望。
军国主义的狂热惯性,以及高层对战争责任的恐惧,使得任何“求和”的提议都等同于“国贼”的言论。
更为致命的是来自柏林的态度已经通过德属东亚总督府清晰地传递了过来。
“彻底推翻日本帝国主义政府,清除其军国主义根基,否则日本将永远成为亚洲和平之毒瘤与威胁。”
这是牢林下达的最高指示,冰冷,坚决,不留丝毫余地。
它像一道最终判决,堵死了日本任何体面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柏林要的不是谈判,不是妥协,而是无条件投降和政权更迭,这意味着天皇制的存续与军部大佬们的命运都将画上问号,这是他们绝对无法接受的。
于是,在绝望的驱使下,日本这架失控的战车,选择了继续冲向深渊。
“一亿玉碎”、“本土决战”的口号被喊得震天响,疯狂的战争动员进一步加剧,连竹枪都被分发到了平民手中。
他们宁愿在“光荣”的毁灭中拥抱集体疯狂,也不愿在理性的屈辱中寻求一线生机。
与此同时,远在欧洲的法兰西公社同样在战争的沉重负担下喘息。
巴黎人民宫内,瓦卢瓦独自坐在办公桌后,窗外是灰蒙蒙的巴黎天空,一如他此刻的心境。他手中拿着一份份令人沮丧的报告,眉头紧锁,仿佛承载着整个欧洲左翼事业的重量。
“究竟……怎样才能获得胜利呢?”
他喃喃自语,这问题如同梦魇,缠绕他已久。
一九四零年德国的反攻计划“曼施坦因计划”让英法两国失去了大量的部队,两国被俘兵力加起来超过五十万,一次战役让英国陆军自此一蹶不振,退回本土后至今未能恢复元气,只能依靠海军和日渐微弱的空军力量进行防御。
法国陆军也也元气大伤,失去了宝贵的战略主动权。
两年过去了,创伤远未愈合。
国内经济一团糟,持续的战争消耗和资源封锁,使得工厂的开工率大幅下降,许多非必要的民用生产早已停止。
如果不是隔着大西洋的美利坚联合工团加大了粮食、石油、武器装备、工业品与部分工业原材料的援助,法兰西公社面临的物资匮乏和社会动荡将更加严重。
但最让瓦卢瓦感到无力的是人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