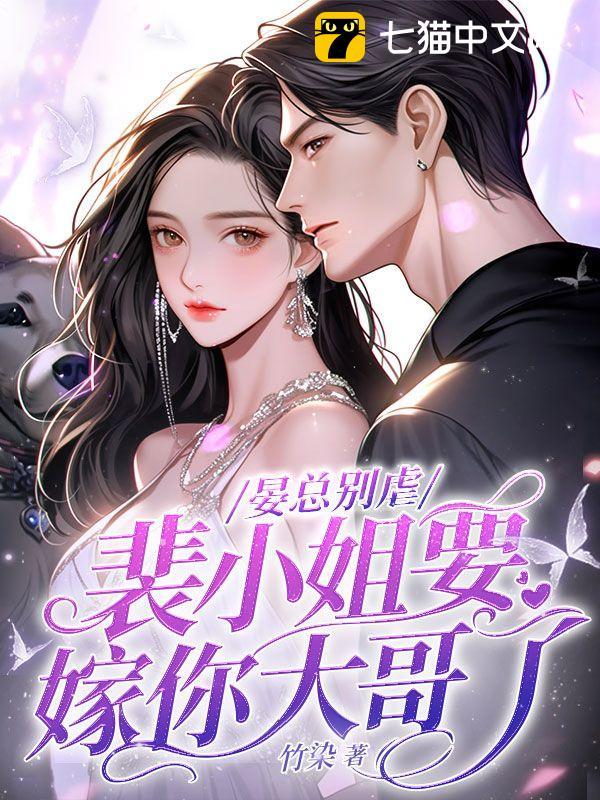久久书库>半夏花开半夏殇 > 第960章 钥匙与茉莉(第1页)
第960章 钥匙与茉莉(第1页)
挂断电话,她却感到一阵更深的空虚。那句“没问题”,像是对自己撒下的一个弥天大谎。
她拿起手机,鬼使神差地,取消了之前对高槿之号码的屏蔽。她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或许只是想确认一下,他是否还会发来那些“普通朋友”的信息?或许只是想看看,在那样难堪的重逢之后,他还会说些什么?
手机屏幕安静如初,没有任何新消息。
这种沉默,反而让她感到更加不安。
高槿之在那天离开许兮若的公寓后,骑着电动车在城里漫无目的地转了很久。初秋的风已经带上了凉意,吹在他脸上,却无法吹散心头的滞闷。
他最终没有回自己的公寓,而是去了向杰的家。向杰打开门,看到他失魂落魄的样子,什么也没问,把他拉进门,递给他一罐冰啤酒。
两个男人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万家灯火。
高槿之断断续续地说了今天发生的事情。向杰听着,没有像往常那样插科打诨或者激烈批判,只是默默地喝着酒。
“槿之,”良久,向杰才开口,声音是罕见的沉稳,“我知道你难受。但今天这事儿,确实是你做得不地道。”
高槿之苦笑了一下,点了点头。
“人家姑娘已经往前走了,有自己的生活。你再去那个地方,还买那些东西……说句不好听的,这叫骚扰。”向杰的话说得很直白,“你那个什么‘从朋友做起’的想法,我一开始就觉得不靠谱。真正的放下,是尊重她的选择,祝福她的生活,然后过好自己的日子。而不是变着法儿地想留在她的生命里,哪怕是以‘朋友’的名义。”
高槿之沉默地听着。向杰的话像一把锤子,敲碎了他最后一点侥幸心理。
“我知道你舍不得,”向杰叹了口气,“那么多年的感情,哪能说忘就忘。但舍不得,也得舍。这不是为了她,是为了你自己。你总得……让自己喘口气吧?”
高槿之仰头灌下最后一口啤酒,冰凉的液体划过喉咙,带来一丝清醒的刺痛。
“我明白了。”他轻声说,声音里带着一种近乎认命的疲惫。
从向杰家离开后,高槿之没有再尝试任何形式的联系。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甚至开始利用休息时间,跟着车队里一位老师傅学习简单的车辆检修。那种需要专注和体力的劳作,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救赎。汗水能暂时冲刷掉脑海中的杂念,解决一个机械故障带来的成就感,虽然微小,却真实。
他也开始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他不再强迫自己记录情绪,而是买了一个素描本,在工作间隙,看到有趣的乘客、街边的风景,或者只是脑子里闪过的一个画面,他会尝试用铅笔把它画下来。画得歪歪扭扭,毫无章法,但在这个过程中,他感受到了一种不同于语言表达的、安静的宣泄。
陈医生肯定了他的这种变化:“用创造性的方式去表达和疏导情绪,是很好的尝试。艺术本身就有疗愈的作用。”
生活似乎真的在朝着一种新的平衡缓慢挪动。他依旧会想起许兮若,想起那些美好的过往,心口依旧会泛起细密的疼痛和深沉的“舍不得”。但他不再试图去对抗或者消除这种情绪,而是学着与它共存,像接纳一个不时会发作的、陈年的旧伤。他不再幻想“朋友”的身份,也不再期待“复合”的可能。他只是努力地,一天一天地过着自己的生活。
偶尔,在驾驶公交车经过某个熟悉的路口,或者闻到某种熟悉的气味时,心脏还是会骤然紧缩。但他学会了在那一刻,深深地呼吸,然后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在前方的道路上。
他知道,那条回响着沉默的隧道依旧很长,很暗。但他不再急于寻找一个明确的出口。他只是调整着自己的呼吸和步伐,适应着这片黑暗,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而许兮若,在取消了屏蔽后的几天里,手机依旧安静。高槿之的沉默,像一种无形的压力,让她在松了口气的同时,又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她开始更频繁地和凯桥见面,努力地投入到现在的关系中,试图用凯桥的稳定和温暖,来填补内心的空洞和不确定。
她和凯桥一起吃饭,看电影,规划着见他父母的细节。她表现得体贴又得体,但只有她自己知道,那种投入总像是隔着一层什么,无法全然沉浸。
有时候,在和凯桥相处的某个瞬间,她的思绪会突然飘远,想到那盆被遗落在鞋柜上的茉莉花,不知道它最后怎么样了。
这种一闪而过的念头,让她感到恐慌,也让她更加用力地握紧凯桥的手,仿佛这样就能抓住眼前确定的幸福。
都市的夜晚依旧灯火璀璨,如同流淌的星河。两段人生,在短暂的、充满张力的交汇之后,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延伸开去。一个在孤独的静默中学习着与过去和解,一个在看似安稳的现实中挣扎着内心的波澜。前路依旧迷雾重重,战争的硝烟并未完全散去,只是化作了更细微、更持久的尘埃,弥漫在每一次呼吸,每一个不经意的闪回里。
寂静,不再是真空,而是充满了未竟之语和复杂情感的、沉重的回响。而他们,都在学习如何背负着这沉重的回响,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