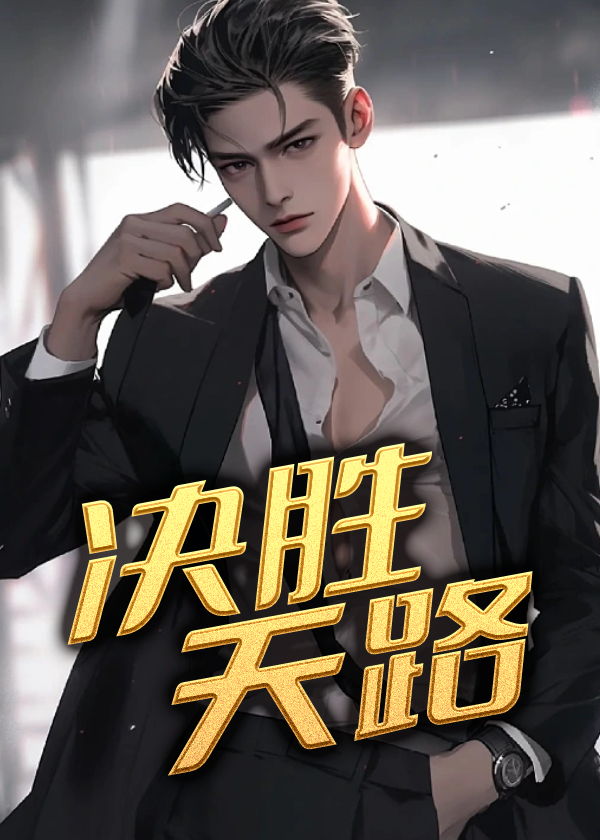久久书库>对弈江山 > 第一千三百三十七章 所做所行皆为良人(第2页)
第一千三百三十七章 所做所行皆为良人(第2页)
“她低垂着眼睑,专注地拨动着怀中的琵琶,十指纤纤,在琴弦上跳跃。琴声从她指尖流淌出来,时而如泣如诉,时而如金戈铁马,竟将一曲《十面埋伏》弹得荡气回肠,完全不像是一个风尘女子所能驾驭的。”
韩惊戈顿了顿,语气中带着一丝当初的惊艳与不解。
“我那时虽醉,但耳朵还没坏。我听得出,这女子的琵琶技艺,绝非寻常乐伎可比,甚至比许多所谓的大家还要精湛。更奇怪的是,她身上没有半分风尘气,反而有一种。。。。。。一种说不清的落寞与孤高。”
“她就那样静静地弹着,仿佛周遭的一切喧嚣都与她无关。”
“一曲终了,满堂喝彩。她却只是微微欠身,抱着琵琶,便要退下。”
“老鸨满脸堆笑地上前,似乎想让她再弹一曲,或是陪客人喝杯酒。她却轻轻摇了摇头,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地说,‘妈妈见谅,阿糜只卖艺,不陪酒。’”
“莫非他就是。。。。。。”浮沉子心中一动道。
“阿糜。。。。。。”
韩惊戈轻轻念出这个名字,声音里带着无尽的眷恋。
“那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听到她的名字。不知为何,那个在喧嚣酒肆中独自弹着苍凉琵琶、坚持‘只卖艺不陪酒’的倔强身影,就那样印在了我的脑海里,连带着那晚的酒,似乎都多了几分不一样的滋味。”
“自那以后,我去‘醉仙居’的次数,似乎更多了。”
韩惊戈继续讲述,语气平缓。
“依旧是为了买醉,但总会下意识地选择能看清舞台的位置。我发现,阿糜并不是每天都来,她似乎很自由,想来便来,想走便走。她弹的曲子也多是些古曲,或是她自己改编的一些带着边塞风霜、江湖意气的调子,与醉仙居那种纸醉金迷的氛围格格不入。”
“客人点她唱些艳曲小调,她总是婉拒。久而久之,虽然欣赏她技艺的人不少,但真正捧场的客人却不多。老鸨对她似乎也无可奈何,大概是签了特殊的契约。”
“我那时心灰意冷,虽然注意到了她的特别,却也并未多想,只是觉得这女子有些意思,在这污浊之地,竟能保持一份难得的清净。”
“直到。。。。。。那年我回京都的第一场雪。”
韩惊戈的眼神变得温暖起来,仿佛被记忆里的雪光映亮。
“那晚雪下得很大,我喝到深夜,醉意醺醺地离开醉仙居。寒风裹着雪花扑面而来,让我打了个激灵。”
“走到街角,却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阿糜。她抱着琵琶,独自一人站在风雪里,似乎在等车,冻得瑟瑟发抖,脸色苍白。她身上那件单薄的冬衣,根本挡不住这彻骨的寒意。”
“鬼使神差地,我走了过去。”
“她看到我,有些警惕地后退了半步。我那时满身酒气,样子想必也很颓唐。我脱下自己身上那件还算厚实的貂皮大氅,递给她,闷声说,‘穿上吧,天冷。’”
“她愣住了,抬头看着我,雪花落在她长长的睫毛上,晶莹剔透。她犹豫了一下,没有接,只是轻声说,‘多谢公子,不必了。’”
“我有些烦躁,或许是酒劲上来了,直接把大氅塞到她怀里,粗声粗气地说,‘让你穿就穿着!冻病了,还怎么弹琵琶?’说完,我也不等她再拒绝,转身就走,踉踉跄跄地消失在风雪里。”
浮沉子呵呵一笑道:“你这手段,简单粗暴啊,比苏凌可是差得远了。。。。。。不过道爷喜欢!。。。。。。”
韩惊戈笑了笑,带着一丝自嘲道:“现在想来,当时的行为真是又鲁莽又可笑。但。。。。。。那大概是我断臂回京后,做的第一件。。。。。。不那么像个行尸走肉的事情。”
“我以为那晚之后,也就如此了。没想到,过了几天,一个午后,我在一家清静的茶楼里喝茶醒酒,又遇到了她。”
韩惊戈的神情,带着当时的意外和欣喜。
“她主动走过来,将我那件大氅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我面前的桌上,轻声道,‘那晚,多谢公子。’”
“我这才看清她的正脸,比在醉仙居灯光下更清秀,眉眼间带着一股书卷气,完全不像个乐伎。她似乎犹豫了一下,在我对面的位置坐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