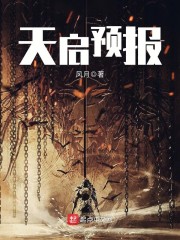久久书库>红楼之老祖宗自救指南 > 第23章 心事(第1页)
第23章 心事(第1页)
碧纱橱内,药香比往日更浓了些。
黛玉斜倚在绣榻上,身上搭着一条薄薄的锦被,脸色苍白,眼下一片淡淡的青影,更显得楚楚可怜。
她手里握着一卷《庄子》,却半晌未曾翻动一页。
紫鹃端着一碗刚煎好的药进来,见她这般模样,心疼道:“姑娘,药好了,趁热喝了吧。”
黛玉恍若未闻,目光怔怔地望着窗外摇曳的竹影。
那些风言风语,终究还是像冷风一样,钻进了她的耳朵里。
“带坏宝玉”“内帷厮混”……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她心上。
她自幼失怙,寄人篱下,心思本就比旁人敏感多疑,此刻更是觉得四面八方都是审视和鄙夷的目光。
是自己……连累宝玉了吗?
若不是自己常与他说话,与他论诗,他或许就不会被那些人如此诟病?
一种熟悉的、自伤自怜的情绪涌了上来,喉头泛起腥甜,她忍不住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撕心裂肺,单薄的身子蜷缩成一团。
紫鹃吓得忙放下药碗,替她拍背顺气,急得眼圈都红了:“姑娘!您这是何苦呢!为那些没影子的话气坏了自己,不值当啊!”
就在这时,门外小丫鬟通报:“老太太来了!”
黛玉一惊,挣扎着要起身,林晞却已经扶着鸳鸯的手走了进来。
林晞一进屋,就闻到那股子沉闷的药味,再看到黛玉那副形销骨立、泪光点点的模样,心里便明白了几分。
她摆摆手,示意黛玉不必起身,自己在榻边的绣墩上坐了。
她没有像往常那样直接安慰“莫要多想”“保重身子”,而是目光温和地打量着这间雅致却难免清冷的屋子,最后落在黛玉手中那卷《庄子上》。
“在看《庄子》?”林晞语气平常,“‘逍遥游’,意境是开阔,可惜太过虚无了些,看多了,易生孤寂之感。”
黛玉垂下眼帘,低声道:“不过是胡乱翻翻,解闷罢了。”
林晞从鸳鸯手中接过一个锦匣,打开,里面是一叠有些年头的花笺,墨迹娟秀。
“这是我年轻时,收集的一些前朝才女的手稿残篇,有诗词,也有游记,甚至还有几篇论政的文章。”
她抽出一张,递给黛玉,“你瞧瞧这个。”
黛玉接过,只见上面写着:“……闻边关告急,粮草匮乏,妾虽女流,愿捐妆奁以助军资,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字迹劲秀,带着一股不让须眉的豪气。
“这是前朝一位将军夫人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