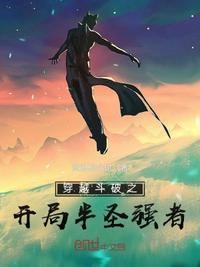久久书库>四合院:我,十岁称霸四合院 > 第836章 土豆买礼物(第2页)
第836章 土豆买礼物(第2页)
她拍了拍刘母的手背,语气恳切:“春晓在医院上班忙,家里的活计不用她沾手,实在忙不过来,还有从卿那小子,让他干。
她要是想回娘家住,抬脚就走,我们保证半句闲话没有。”
刘母听得眼眶有点热,笑着拍了拍她的手:“瞧你说的,多外道。
咱们住一个院多少年了,你们的为人我还不清楚?
春晓能嫁到你们家,是她的福气,我一百个放心。”
刘父在一旁点头附和:“孩子们从小一起长大,知根知底,日子肯定能过好。
至于结婚的日子,我跟她妈商量了,六月十九就挺好,顺顺当当。”
顾父连忙应道:“好日子,就听你们的!
到时候就在从卿爷爷那大院摆几桌,都是自家人,热热闹闹的就行。”
周姥姥笑着插话:“嫁妆啥的也别费心,孩子们过日子,实用最要紧。
我都给春晓备了两床新被面,棉花是新弹的,软和着呢。”
刘母摆手:“您太周到了。
我们也没啥讲究,就盼着俩孩子往后互相疼惜,把小日子过踏实了。”
两家人你一言我一语,从日子说到住处,从家务说到回门,句句都落在实在处。
临走时,刘母往顾母手里塞了包自己晒的干菜:“拿回去炖肉吃,春晓最爱这口。”
顾母接过来,笑着应:“哎,等她嫁过来,我天天给她做!”
一行人往回走,周姥姥哼起了小曲,顾父顾母相视而笑。
孩子们的婚事就这么定了。
婚期定在了六月十九,周日。
周姥姥特意弄了张张黄历回来,指着“宜嫁娶”三个字笑得合不拢嘴:“你看这日子,天头肯定好,街坊邻居也都歇着,来喝喜酒也方便。”
顾从卿和刘春晓听了都没意见,只觉得这日子透着股踏实的喜气。
院里的红灯笼已经开始张罗着糊了,何雨柱的菜单改了三稿,连供销社的同志都知道顾家要办喜事,见了顾母总笑着问:“糖票备够了没?”
院里最忙的反倒不是要结婚的两人,而是土豆。
这小子自从回了学校,就像憋着股劲的小炮仗。
那天放学回来,书包往炕上一摔,气鼓鼓地说:“班里王甜甜说我在乡下待傻了,考试肯定不如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