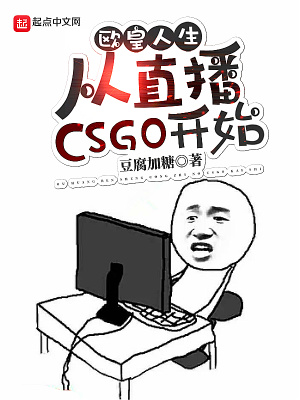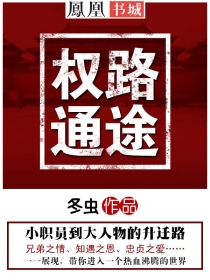久久书库>大明:哥,和尚没前途,咱造反吧 > 第一千二百四十二章 并行与换拍(第2页)
第一千二百四十二章 并行与换拍(第2页)
他站在圈外,先看,后点,再收。
点得极少,收得极稳。
到第三回时,那口吃的学子说话不再磕绊,声音比前一日圆了不少。
“王爷。”白簪来到石边,轻声,“白榆,自个儿带了一小队孩子,往西巷去了。”
“他愿意带人了。”朱瀚点头,“好。”
“他走之前,停在‘收得回’这里看了很久。”
白簪道,“他把手按在石上,又放下。”
“他与自己说了一句‘我到了’。”朱瀚笑。
白簪眼神一动,随后也笑:“王爷,石边有一个人,眼睛一直盯着字看,很静。他脚步像拆了又装过。”
“去看看鞋跟。”朱瀚道。
白簪点头而去。
午后,院内渐渐人多。有人从外城赶来,喘着气在石前站住,眼睛在三行字上走来走去。
也有人在旁边的小筐里翻瓦片,翻出一片空白的,执笔写下小小两个字:“试试”。
写完,把瓦片垫到石座下。
“殿下。”老人忽然站起,把竹尺递到朱标手里,“你来写一笔。”
“写什么?”朱标问。
“写‘久见常’。”老人笑,“那日王爷写了‘久常’,我看着手痒。”
朱标受了竹尺,站在第三块石旁,仰面看了一眼,才落笔。
刻毕,人群里忽有掌声。掌声不大,像细雨。
朱瀚侧耳,心里的“回声图”一展,脚步的密度像点点墨落在绢上——最密的一团,在石前右侧。
那里站着一个青年,衣著朴素,鞋底厚实,双手搭在自己腰侧。他在看字,也在看人。他的脚步之前乱,如今很稳。
“他会开口。”朱瀚在心里道。
果然,青年抱拳走到石前,声线不高:“殿下、王爷。小人做货郎,走南走北(他立刻改了口)——走城内城外,脚底的路多。今日看了这‘收得回’,念起来,心里就不慌了。我不懂书,但我懂一个‘回’字,该回就回。”
“说得好。”朱瀚点头,“你叫什么?”
“李合。”青年答。
“合线的‘合’?”朱瀚笑。
“是。”李合也笑,“我爹起名图个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