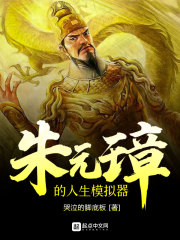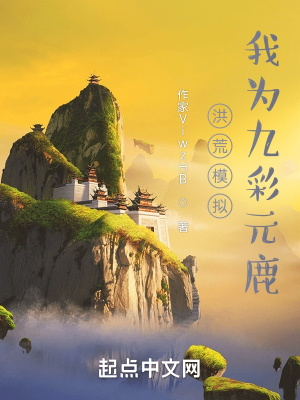久久书库>满唐华彩 > 第605章 顽疾(第5页)
第605章 顽疾(第5页)
如今有些地方官,或把春苗贷贪了,或是贷给亲眷放高利贷的,或是干脆怠政不作为的,这也是为何是由丰汇行来批这笔钱,但天下还是有很多小州县,丰汇行没覆盖到或没那个人力。
“寿安县办得不错就好。”杜五郎又转向袁志远,问道:“你呢?考试准备得如何?”
“学生有信心。”
袁志远应了,想了想,还是问道:“郎君,我听说崔家因为我而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了?”
提到此事,杜五郎便觉得对崔洞有些愧疚。
袁志远中了县试,他为何成为崔家的奴隶之事也被翻了出来。
崔家利用灾年,借出一斛粮食就买下了当年老袁头所有的田地,后来连人也买为奴婢。这数十年间,像这样逃户被匿藏为奴的,数不胜数。
包括,朝廷削减寺庙时,崔家还包庇了不少僧人。
这些不算是大罪过,高门大户普遍都是这么做,但树典型就是这样,崔家恰好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只能自认倒霉。
杜五郎已不能出于朋友之义帮崔洞一把了,因为知道薛白想要借着这件事施行新政。
这次只怕不是小的改革,而是税法。
当然,朝廷上只怕会有不小的反对力量。
“并不是因为你。”杜五郎回过神来,对袁志远道:“而因为……大势所趋吧。”
~~
次日,袁志远从洛阳回到了县学。
号舍中,林济正在与同窗讨论着什么。
“要我说,变乱的根由在于田地兼并。”
“高门豪族兼并良田、隐匿人口,朝廷收不上来税,开支却与日俱增,国库没钱,对地方的管控力自然就变弱,乱象自生。”
“若要根除积弊,无非两个办法,一则清丈田亩,按田地多寡收税;二则,干脆将田地收归朝廷,重新划分……”
袁志远问道:“你们在说什么?”
林济回过头来。
他还很年轻,虽然总是故作老成,但神态话语里还是难免流露出一些稚气未脱,想法也有些天真。
但他拥有的是一腔热忱。
“我们在谈策论的题目,对租庸调革弊去新!”
袁志远问道:“这是先生出的题吗?”
“不。”林济道,“这是今年春闱的题。”
他们还没有考进士的资格,袁志远总觉得那还很遥远,他得再通过两次考试,或许才有资格到国子监读书,然后参加省试。
备考到如今,他已渐渐没了心力,因为意识到自己与那些生员的差距太大了。
就连对比林济,他也自愧不如,林济虽出身贫寒,但读的是济民社的学堂,所学的都是经邦济世之道。而他,花了太多时间揣摩怎么服侍主家,杂念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