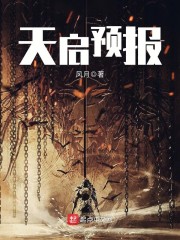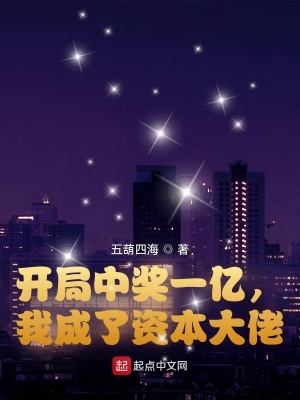久久书库>代晋 > 第一三八六章 手段二合一(第2页)
第一三八六章 手段二合一(第2页)
在思虑之后,桓玄将目标锁定在了豫章郡的刘裕,以及目前在南阳郡颇为活跃的殷仲堪之子殷旷之,还有在梁州作乱的巴獠身上。
之前桓玄并没有太在意这三股势力,只是想集中力量先对付徐州李徽。毕竟李徽是头号心腹大患,其余三股势力其实都不足为虑。但李徽这块硬骨头目前是啃不动了,那便退而求其次,先解决这些后方割据作乱之徒。
这么做也是有极大的意义的,可以挽回军事上的失败,对冲京口之败带来的影响。这就好像当年桓玄的父亲桓温所做的那般,在坊头大败之后,桓温为了挽回失败带来的影响,立刻率军去攻寿春,将袁真攻灭。将豫州地盘和兵马攫取入囊中。既震慑了大晋上下,展现了武力,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地盘和兵马。
桓玄这么做,和桓温当年的决定一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另外,攻灭这些割据反叛势力更具有较为现实的意义。
刘裕在豫章最
近闹腾的厉害,豫章郡左近的临川郡等十几个郡县都为刘裕所据。江州中部之地已经都为刘裕所有,所辖人口数十万之众。
那刘裕还占据了鄱阳湖水面,数十艘水军战船时常滋扰鄱阳湖北侧的寻阳一带。这厮煽动江州百姓,四处诋毁荆州兵马,说什么桓氏篡逆,挟天子以令天下,迟早篡位谋国,他要为大晋铲除野心之贼云云。
关键是,刘裕占据江州中部,控制鄱阳湖水道,给桓玄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荆梁益三州乃是桓玄的后盾,桓氏在此根基颇稳,也是荆州军钱粮人力物资供应的主要来源。但是西北距建康太远,兵马物资供应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通过大江水道自然是最为快捷的办法,但是李徽的兵马控制了江淮水道,之前达成协议,倒是可以畅通无阻。但是现在京口之战后,双方事实上已经是敌对状态,东府军随时会截断水道,让在京城的荆州兵马难以得到荆州和西北方向的支援。
对桓玄而言,这是极大危机。既然暂时不打算再攻李徽,则必须要找到一个替代的路线。实际上,大江以南的陆路,穿过江州中部官道运输物资粮草和兵马的补充也是可行的。这样便可以避免大江水道被截断的风险。
而刘裕则正好卡住了江州中部,控制了鄱阳湖,好死不死的成为截断路上通道的一股势力。
对于桓玄而言,刘裕那点兵马其实不值一提,他只是之前的目标不在刘裕身上罢了。但现在,解决刘裕就成了既打通陆上通道,利于物资粮草兵马从西北运抵京城的最佳方案,也同时成了军事上立威的必然选择。
至于南阳的殷旷之和梁州作乱的巴獠部落,那不过是为了更好的平复荆州和梁州的局势,解决这些令人作痒的疥癣之疾罢了。
以上是军事方面的考虑,挽回军威,打通通道,为之后做准备。另一方面,桓玄要解决的便是朝中那些沉渣泛起的反对之声,以及一些妄图借司马德宗的名义抱团和自己作对之人。
桓玄认为,必须要严厉的惩罚朝中这些想要挣脱自己的掌控,觉得局面有变,可以和自己掰掰手腕之人。特别是司马德宗和他身后的一些人,要将这些人全部扫除清理,将司马德宗牢牢的掌控在手中。
除了铲除这些异己立威之外,掌控司马德宗便是掌控住大晋朝廷。这对于李徽也是一种牵制。桓玄此刻最担心的便是司马德宗跟李徽搞到一起,偷偷给李徽下个诏书什么的,让李徽率军进攻京城,并且赋予他皇命。那样的话,李徽便可肆无忌惮的进攻了。
必须杜绝这种可能,那便要将朝廷再一次的整肃,将一些人铲除。要将司马德宗软禁起来,不许他见到任何人,彻底的杜绝司马德宗和其他人接触的可能。
在经过长达半个月的思索之后,桓玄确定了这个计划,他首先开始了他的大清洗行动。
正月二十之夜,桓伟率领一万中军兵马全城发动,一夜之间抓捕了四十多名朝中军政官员和京城大族。并封锁了皇宫,撤换了所有司马德宗身边之人。
清晨时分,桓玄召集朝会,宣读了司马德宗的圣旨。圣旨之中,将被抓捕的四十余名朝中官员和京城大族一律归为司马道子遗毒同党。以王绪之前策划诱杀周澈之事作为殷鉴,表示要彻底清除司马道子遗毒同党,以免再一次发生阴谋策划挑拨离间诱发大晋内斗之事。要严惩所有
被抓捕的这些人和他们的亲眷。
所有人都噤若寒蝉,在桓玄询问他们有无反对意见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说话。因为所有人都明白,这是桓玄一手策划的大清洗行动。圣旨不过是个幌子,陛下都没有出席这次朝会,这圣旨显然是矫诏行为。
那些被抓捕的人之中,有一部分还是对桓玄溜须拍马极尽谄媚之人。所有人都没有任何的实际证据和不轨的行为,只是完全凭借桓玄的臆断便将他们全部缉拿。
没有任何的审判程序,很快,桓玄便宣布将这四十余族近三百人全部斩首示众。正月二十二上午,在朱雀大街街口的寒风之中,这三百余人无论男女老幼全部被当街斩首。其中最小的孩童尚在襁褓之中,也被行刑的刀斧手一砍两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