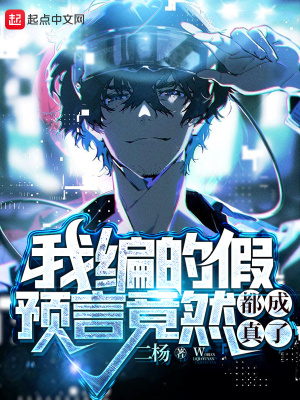久久书库>北宋小丫鬟 > 第140章(第2页)
第140章(第2页)
锦娘含笑:“我要先等六月再答复您,现下我也不知晓。”
她也不能胡乱给人做全福人,万一这家名声不好就不好了。
庞太太见锦娘头戴三凤衔珠的步摇,手上戴着茉莉花串,身上衣裳精美繁复,就忍不住鼓起勇气,不曾想人家完全没有拒绝。
锦娘差人去打听庞家如何,又见弟弟一家进京了,让厨下准备接风宴。
这五六年来,对于锦娘似乎没什么太多不同,但是对于弟弟魏扬而言,算是彻底从一个学生进入社会。但见他身上气质愈发干练,锦娘欣慰道:“看着你们这般,我比什么都高兴。”
弟妹张氏这几年生了一儿一女,长女叫梓怡,今年四岁,儿子才刚长牙,罗玉娥把两个孙子看的跟心肝宝贝似的。
锦娘这里给侄女送了一顶金项圈,给侄儿送了一对玉牌。
张平君笑道:“我们知晓筠姐儿的事情,这次回来特地备下好多东西给她添妆。”
“哪里要你们准备,我这几年旁的事情都没做,专门就在备嫁妆。”
锦娘道。
大家纷纷入席,男女分开,男人们去过厅那边用的,吃酒谈天,女人们则坐在一桌吃饭。罗玉娥还是一样,无论锦娘提什么,她都可以准确无误的转到扬哥儿身上。
“你弟弟那时候也是一个人住书院,但是我和你爹也是送饭的,你弟弟呀,和别人处的都好……”
锦娘有些无奈道:“娘,我现在说的是我们家宁哥儿,扬哥儿的事情我又不是不知道,您都说过八百遍了。”
罗玉娥这才反应过来,“知道了,知道了,我一时忘形。”
筠姐儿心想娘要经营这个家真不容易,都不知晓怎么熬过来的,她虽然有两个弟弟。但是娘对他们一视同仁,不会这样对着一个孩子不停的念叨另一个孩子。
论及孝顺,她想娘比舅舅要孝顺许多,自己建了宅子就把爹娘接着住。
舅舅的前途也是爹运作的,和魏家联姻多了一份依靠,娘的功劳这般大,却很少在外祖母嘴里提起。
桌上很快恢复正常,饭毕,张平君给筠姐儿送了两抬嫁妆,有宣州的徽墨,宣笔、宣扇、徽砚,杭州的丝绸六匹,描金妆奁盒一个、妆粉两匣,绢花三十六枝。
筠姐儿想这还没有姚掌柜和大名府塌房掌柜,甚至是如烟送的多。
好在留她们住了一晚,魏扬夫妻去了张氏的宅子里,罗玉娥夫妻则去了田庄住,没有再住锦娘这边。
锦娘一看女儿神情就明白了,她笑道:“上回我让你舅母把家俬搬走,恐怕她就觉得我见外了。”
“可是舅舅也是爹拉拔在京中的啊?”
筠姐儿不明白。
锦娘笑道:“但是你想你舅舅外放这六年,可都是你舅母在打点,连同跟着去的师爷,傔从,这些费用可不菲,我们也没有帮什么忙啊。你舅母这么些年也不容易,她嫁妆虽然丰厚,但是你跟娘打理过家务,每年咱们送礼,单上下打点就耗一笔钱啊,你舅舅虽然有俸禄,总得仰仗她。”
“再有周家的事情,周家和我们是姻亲,周家大奶奶是她姑母,咱们袖手旁观,她岂有不知道的?但这些是我帮她找的理由,究其根本还是一句话,施恩莫图报,因为十成人中有九成人都不会回报。”
永远降低对别人的期待,自己活的自私一些,多为自己想一些就好。
筠姐儿知晓舅母其实也对她不错,外祖母和外祖父方才临走时,还记得自己爱吃什么。但总归是两家人了……
锦娘却想以前家里人都听自己的,那是因为她最有钱,所以是话事人,现在这个话事人已经转移到张氏身上了。
便是她自己,如今宁哥儿定哥儿都很黏着她,但将来他们成婚,也会有各自的小家。
这也是锦娘始终要留四千两的金子傍身的缘故。
但她也知晓女儿还年轻,性格是非分明,日后她就明白了,人都是很复杂的。无论是父母还是男女之情,太过纯粹的,只存在于书上,寻常人很难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