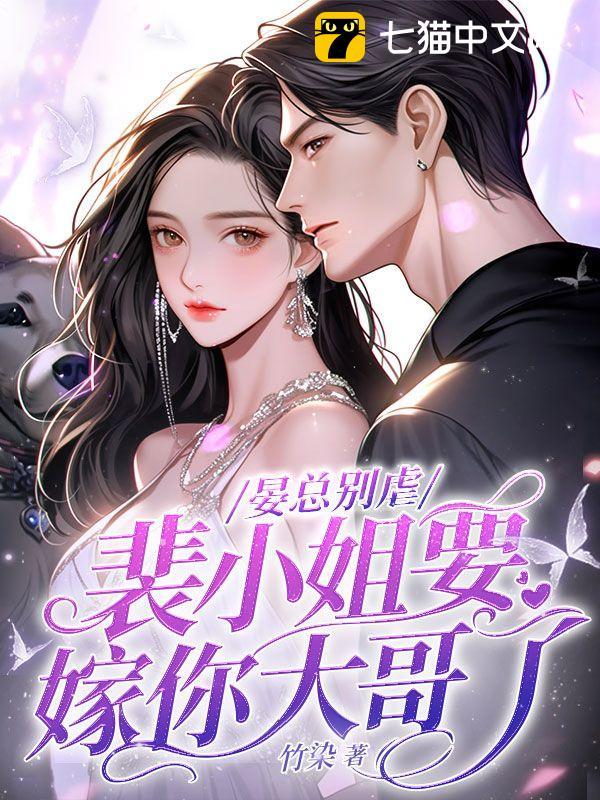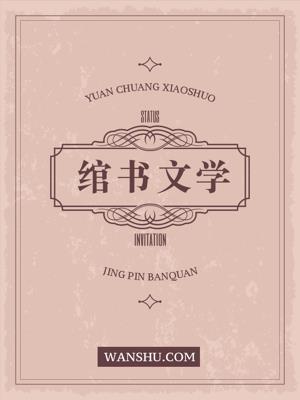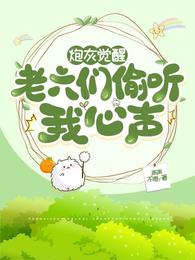久久书库>崇祯,师叔来教你做皇帝 > 第134章 少年考进士吧(第2页)
第134章 少年考进士吧(第2页)
“目前只有一个学堂,所以,就取名叫做行知堂。”韩庆之丝毫不怯场,面对正二品礼部侍郎,福建巡抚朱一冯,侃侃而谈,“取的是知行合一的意思,希望孩子们不但能读书明理,还要做到行为与所学一致。”(注:明代巡抚,加了侍郎头衔为正二品,否则为从二品。)
“好,好!”朱一冯听了,再度高兴地抚掌,“知行合一,知行合一,这个名字有气魄,韩守备也的确有眼力。”
“就是卑职的字太丑了,所以一直没敢写匾额。”韩庆之忽然又开了窍,讪讪地拱手,“卑职有个不情之请,还望巡抚恩准。”
“说吧,只要与不违背国法与公序良俗,老夫就可以答应。”朱一冯心有灵犀,手捋胡须,轻轻点头。
“那卑职就僭越了。还请巡抚为学堂提写匾额,以鼓励蒙童们认真向学。”韩庆之接过话头,长揖及地。
“好,老夫就成全了你。”朱一冯毫不客气地受了他的全礼,然后吩咐笔墨伺候。
立刻有亲兵蹑手蹑脚地走进学堂,跟教书先生去借笔墨。那教书的先生姓李,单名一个方字,乃是个屡试不中的秀才,读书读成了高度近视眼。
先前只察觉有一大堆人站在了学堂外,还以为是前来购买香烟的商贩,故意附庸风雅。所以他才刻意安排学子们将《正气歌》给背诵了出来。
此刻听闻,来的是曾经的二甲进士,福建巡抚朱一冯,他顿时慌了手脚。一边抬起衣袖抹汗,一边亲手将笔墨献上。
“你教的很好,读书人肚子里就应该有一腔正气。特别是开蒙阶段,一定要扶正祛邪,在孩子们心中播下正气的种子。”朱一冯见多识广,也不计较教书先生李方刚才的怠慢,接过毛笔,笑着鼓励。
“抚台过奖了,学生不胜惭愧!”李方被夸得骨头都轻了三分,红着脸拱手。
朱一冯听了学生两个字,立刻知道他是有秀才功名在身的。笑了笑,再度轻轻点头,“并非过奖,老夫刚才听你指点蒙童,很多说辞,都与儒家精义相合,想必下过一番苦功的。来年又是大比之年,你何不再下场放手一搏?即使一时不慎,发挥不出平素的半成水准,终究也是尽了全力,心中不留遗憾。”
“多谢抚台鼓励,学生一定不辜负您的期待!”李方听了,被感动得浑身颤抖,含着眼泪,毕恭毕敬地行礼。
众随行官员以目互视,都从彼此脸上,看到了几分困惑。
李方教书教得的确不错,但不一定时文就做出色。
而举人考试,纵然在福建这文教不兴之地,也是上百名秀才里头才能录取一个。(注:时文,就是八股文。)
所以,每届中举者,非但八股文要做得有功力,运气、家世、人脉,也要够分量才行。寒门出贵子,早就沦为对读书人的安慰之言,在福建,甚至整个大明,近三十年都没听说过一个。
再看那李方,又何德何能,竟然凭着教蒙童背了一首正气歌,就博得了巡抚的亲口嘉勉?
有了巡抚朱一冯这几句话,只要他考得不太差,哪个主考官,又能再因为他家世一般,缺乏人脉,就将他拒之门外?
换句简单的话说,巡抚朱一冯今天等于亲手送给李方一个举人功名,就看他本人接不接得住!
然而,令众人看不懂的事情,紧跟着就发生了。
只见那福建巡抚朱一冯,提起笔,龙飞凤舞地写了两个大字,“行知”,然后将笔朝临时搬来的书案上一放,笑着向韩庆之说道,“还有你,韩守备。你既然能说出知行合一四个字来,想必知道其出处在哪。当年乐山居士可是文武双全,以军功封新建伯。你既然以乐山居士为楷模,何不也下场一搏?”(注:乐山居士,是王阳明的别号。)
“考进士,我?”千算万算,韩庆之没想到朱一冯居然对自己提出了如此离谱的一个要求,顿时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老夫夸你有些本事,你就真的不知道自己斤两了。”朱一冯心情正好,笑着摇头数落,“今年匆忙下场参加童子试,明年便能金榜题名者,古往今来,能有几人?”
韩庆之闻听,愈发满头雾水,瞪圆了眼睛无法回应。
看出他是真心不懂,朱一冯笑了笑,继续补充,“武科不同于文科。按本朝规矩,你已经是实职守备,就不需要再考童子试了。刚好今年十月有举人试,老夫的意思是,你尽可以去放手一搏!”
稍稍给了韩庆之一点时间消化,他略作停顿,继续耐心地点拨,“而武科会试,每隔三年才有一次。去年刚刚考过,你即便本事再大,想考武进士,也是后年的事情了。这期间,你刚好把自己的短板补上一补。我朝虽然也讲究,功名但在马上取。然而老夫却以为,还是科场走一遭,博个金榜题名,才是正途。”(注:武科,明代武科不受重视,但武科一直存在。著名的武举人有熊廷弼和俞大猷,史可法则高中过武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