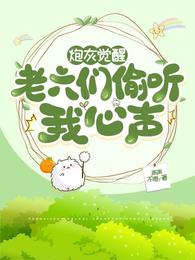久久书库>文豪1983 > 第234章 如何进行文学研究(第2页)
第234章 如何进行文学研究(第2页)
《钟山》的编辑苏彤形容这一篇文章是“文学爱好者进阶的读物,知道这些方法,就基本上能有个章法了,余切真是为读者们用心良苦,上了一盘好菜!”
然而,文章虽然有水平,却吓退不了文学“民科”们的热情,饱含真挚和渴望的信件,源源不断的寄往《十月》编辑部,寄往《人民文学》,寄往《京城文艺》,而信件的收件人只有“余切”二字。
每隔一周,寄给余切的信件需要用小汽车来运送。
《十月》新上任的总编苏玉很尴尬,苦笑道:“大众的文学热情是值得被鼓励的,但他们的文章价值是几乎没有的,为了勘误和回复这些信件,我们几乎再也不能做其他的事情。”
徐驰正是《外国文学研究》的总编,他也为这种情况感到抱歉:“我们的初衷是让社会重新认识文学创作者,激发他们对这一行业的热情,但现在效果好的有些过头了,我们忽然有了八亿小说家,八亿评论家,因为全国人口剩下的两亿,他们还没有学会书写三千个汉字。”
余切只能苦笑了:这一场由报告文《人们想要成为余切》引发的文学效应,竟然比他获得芥川奖还要明显。85年正是文学极盛的一年,就算是《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局外人》这些纯文学也能让读者爱不释卷。
何况是一个他们能真正参与到讨论的文学?
文学研究院进修班的学员们被抓壮丁,纷纷来代替余切给读者们回信。那么多的信件,余切一个人是回不过来的。
余桦、苏彤几个倒是开心,天天不亦乐乎,就像教堂里面的神父,光明正大的看到了很多全国各地的稀奇事儿:什么拿《百年孤独》当小黄书看的;把魔幻现实主义当作YY爽文的……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余切、余切、余切……他们纷纷代替余切回信,一些进修班的作家许多年后仍然记得这一幕,引以为笑谈。
东城,沙滩北街。
《文艺报》的主编冯木正在当项目监工,负责监督新起的《文艺报》杂志社的办公楼。这个国内最高的文艺理论期刊,目前和作协、文联等许多组织挤在一起办公,全报上下只有两层楼可用,也没有自己的食堂。
上一次余切来他们报社拜访,让冯木相当尴尬:余切成名后在哪里都受到优待,但是在他们这里,连吃一口热饭都不行。
现在这种尴尬终于要结束了!
最迟到明年,《文艺报》就能得到搬迁。在领导的关照下,《文艺报》的加刊《文艺理论》成为《内参》一样的读物,每每有什么文学风向,就能通过文章直接传达到上面。
《人们想要成为余切》也被《文艺报》转载,想必已经有许多首长看过这一篇文章。见识到青年作家的风采。
一想到这里,冯木心里就十分畅快。
文学越来越好是十分明显的,有足够多的小说之后,对于这些小说的评定也就变得越发重要,于是文艺批评诞生了——小说评论家的地位也变得重要了。
余切此人的发达,实在是令大家都有好处。
“春雨行动”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长达半年的造势,数百万的筹款,几乎让文学家重新赢得了大众的信任,写小说正在前所未有的成为被尊重的事情。南方的《光明日报》有署名称:“今天的文学不需要救国图存,也不太要做当世警钟……”
“反映社会思潮变化、见证历史事件……当然也大有用处,但缺少了一些个人的积极性和伟大抱负。”
“春雨行动,使得文学家们以恰当的影响力,发扬社会的真善美,这实在是不能不被称为是壮举!”
摸着黝黑的砖瓦墙面,冯木爬上二楼,发觉副主编鲁孙正带着几个编辑看文章。几个人看的格外仔细,脸蛋都通红了,呼吸都快要忘记。
“你看什么呢?”冯木好奇道。
鲁孙抬头一看:哟,主编来了。
顿时就把手上的稿子一扬:《如何进行文学研究》。
他没有说是余切写的。
冯木顿时眼睛一眯,一睁:
这名字取的,不可为不大啊。在论文当中,越是简单的名字,越是代表一些了不得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