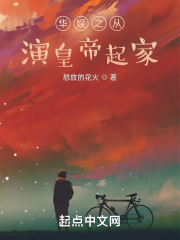久久书库>文豪1983 > 第125章 当余旋风结束大章一笔会剧情完(第3页)
第125章 当余旋风结束大章一笔会剧情完(第3页)
余切是会演讲的,鲁迅是最著名的中国文学家,燕大同样是类比于东京大学的最高学府,除了这之外简直没有更好的例子。
“北”和“大”两个篆体字,叠在上面。
“两个篆体字,表示以人为本,这是大学本来的理念,其次是当时中国积贫积弱,这个标志像人在背负什么东西,鲁迅号召学生们要背负起责任……但最为直观的是,它看起来像‘三个人’。”
“三,在中国有‘众’的意思,三就是无数了,为什么三个人要围在一起?它代表团结,它代表的众志成城,但我们还不能直接从一个校徽,说中国的民族性是‘团结’,它太白了太牵强,而且具备字面上的主观含义,团结的目的是什么?谁能告诉我?”
“我需要一个中性的词汇,它不具备主观的含义,它描述一种状态。”
中哲会里面有许多懂得中国文化的专家,也许余切都能用中文来进行演讲。
立刻有这么一些答案出来:
池田温认为,目的是天下大同。
尾上兼英表示,目的是克服困难,打败强敌,说白了就是抗日。
蜂尾邦夫觉得,团结是结果,是规范和制度的结果。
松丸道雄研究甲骨文,在甲骨文里面,“团”是建造一个篱笆,把人围在里面,“结”是一群人去采集东西回来,他认为这是为共同的利益而行动。
他们都没有错,但余切给的答案和他们都不一样,余切说,“团结的背后是秩序。”
秩序?
好像是这么回事,又好像不完全这样。
天下、礼仪、外敌、和规范……他们和秩序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
余切接下来又解释:“如果没有秩序,就再造秩序,如果秩序不好,就推翻了重新来,这种对于秩序的追求并不是被动服从,而是有暴力性质的——我们把那些平定天下,并且使得社会最终恢复了秩序的人,称之为真正的英雄和伟人。我们的民族,歌颂这样的人。”
“请注意,这和日本并不一样,尽管对于秩序的追求,在不同民族身上都存在,但在中国人的身上,它是尤其明显的。”
他还引入了松丸道雄研究甲骨文的结果:“在中国古人创造出甲骨文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文字,努力的刻在光滑的龟背上,并且写成了一排、一列,方方正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表现出对秩序的追求。”
眼下的人都是真正的专家,他们深耕多年,不完全认同余切的想法。
除了子弹,没有什么观点能让他们纳头便拜,五体投地。
但这几句话一出来,就知道余切真有两把刷子。
作为研究左翼文学的专家,尾上兼英认同这一句话,起码这是中国民族性的一个关键方面。
天下大同,或者是崛起于世界之巅,解放全人类这些东西,当然是当时中国左翼作家的共同愿望,任何一个民族都会这么想,但这些都还太遥远。
他们一开始的渴求,是“恢复秩序”,这个民族不要再这么乱下去了。
当一个国度的文学家们都这么想的时候,把它作为民族性并不过分。
那么,日本人的民族性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