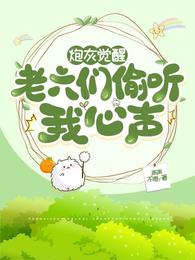久久书库>大明:开局请朱元璋退位 > 第三百三十七章 情报的遗漏消息(第5页)
第三百三十七章 情报的遗漏消息(第5页)
如同被反复筛过的沙砾,只留下最粗粝的部分。
若是平常时日,只有一个藩王在京,类似这种藩王私下活动、与宫内之人暗通款曲的事,或许还会被当作要紧之事,大书特书地写入简报,呈交给他这个皇帝亲阅。
可如今,十几位藩王齐聚京城,光是他们这些人每日的动向、会晤、交游,如果全部事无巨细地汇报上来,那简报的篇幅便要被挤占大半。
故而,下面的人,才没有将周王之事写入《每日简报》上报。
锦衣卫密探和检校就截然不同了。
他们依旧遵循着老朱定下的铁律,按部就班地运行,事无巨细,皆一一如实汇报,不敢有丝毫隐瞒与懈怠。
所以,朱允熥才会在锦衣卫密探和检校递交的情报上,一眼捕捉到这一关键信息。
而探听司和军情处的简报,则因精简的要求,直接将这至关重要的内容忽略而过。
不过,细细想来,也只是没有上报给他这个皇帝而已。
姚广孝既然已经做了批示,就说明下面的人还是有跟进处理的。
只是这是今天才突发的状况,处理起来,自然没有那么迅速。
何况此事牵涉到宫里和藩王,必须慎之又慎,容不得半点马虎。
想到这里,朱允熥那紧皱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
心中的怒气才如同退潮的海水,渐渐消去。
他最忌惮、最担心的事情,便是自己亲手打造的情报机构,有朝一日脱离了自己的掌控,沦为他人操弄权谋的工具,做出瞒上不报的忤逆之事。
只要不是这等恶劣的情形,那便如那船行水上,虽有波澜,却也无伤大雅。
身为帝王,朱允熥每日需处理的事务多如牛毛,不可能将所有的事情事无巨细全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很多事情,只能放权下去。
让下面的能臣干吏自行斟酌处理。
不过,此事仍然如一记警钟,在他耳畔轰然敲响,给他提了一个醒。
“传旨,从今日起,凡军情处和探听司及大明情报局的所有情报,皆抄送一份入静心斋。”
朱允熥深知,必须要防患于未然,防止下面的人,借着情报汇总的契机,心怀鬼胎,将重要的情报隐去不报。
毕竟,摘取哪些情报上报,下面汇总之人,手中握着自主决定权。
而这,极有可能就会滋生出“弄权”的恶果。
还有可能因为个人的疏忽大意,遗漏掉重要的情报,从而错失应对危机的先机。
送入静心斋,由里面那些与世隔绝的女子再整理第二遍,就能极大的避免这一隐患状况出现。
反正进入静心斋的女子,一经踏入,便与外界斩断了所有联系,终身不许再踏出半步,亦不许与外界再有任何联络。
如此,也不用担心她们泄露机密,或者里通外敌。
由她们再汇总审查第二遍,便是上了一道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