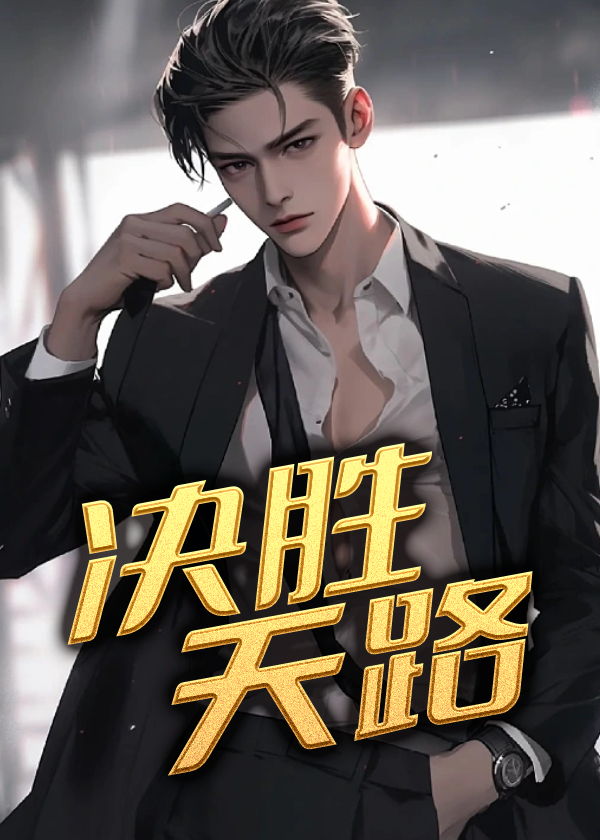久久书库>七零军婚绝美女配把仇人挫骨扬灰 > 第880章 真相来临二(第1页)
第880章 真相来临二(第1页)
一周的西北之行,像一场裹挟着黄沙与希望的跋涉,终于在陆建国和孙凤英踏上京都站台的那一刻暂告一段落。
列车轮与铁轨摩擦的最后一声“哐当”消散在喧嚣的车站里,两人拎着磨得发亮的旧帆布包,衣角还沾着大西北特有的沙粒,眼神却比来时更加焦灼——在李凤银所在的大队,那份关于“女儿”的猜想,已经像藤蔓般在心底疯长,缠绕着他们每一次呼吸。
“老陆,你说……亚男那孩子,真能是咱们的囡囡吗?”孙凤英攥着帆布包的带子,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颤抖。
她的目光越过熙攘的人群,仿佛能直接看到京大校园里那个素未谋面的女孩。
出发去西北前,她夜里总睡不着,一遍遍摩挲着家里仅存的、刚出生时给女儿织的小毛衣,针脚早已被岁月磨得模糊;
而此刻,李凤银递来的那张登在地方报纸上的照片,却清晰得仿佛就贴在眼前——照片里的王亚男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梳着整齐的麻花辫,眉眼弯弯的样子,像极了自己二十岁时的模样。
陆建国拍了拍妻子的肩膀,掌心的温度带着安抚的力量。
他比孙凤英要沉稳些,但眼底的红血丝却暴露了内心的波澜:“咱们先去见吴振华,他在京大当老师,总能想办法让咱们见上孩子一面。
至于是不是,查过就知道了。”
话虽如此,他心里也早已掀起了惊涛骇浪。
在西北黄沙镇的那些日子,他们几乎是“地毯式”地排查当年的线索,光是妻子生产那天的医院档案,就托了三层关系才拿到手。
档案上写得明明白白,那年深秋的那个夜晚,医院里一共降生了四个女婴,这成了他们寻亲的唯一方向。
为了这四个名字,他们跑遍了黄沙镇周边的三个大队。
第一个女孩家在离镇子十里地的王家坳,上门时,院子里正晒着玉米,一个穿着碎花棉袄的年轻媳妇正抱着孩子喂奶,看到他们时,眼神里满是警惕。
陆建国说明来意,那媳妇愣了半天,才讷讷地说自己十六岁就嫁过来了,孩子都两岁了。
孙凤英看着她粗糙的双手、冻得通红的脸颊,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疼,她强忍着眼泪,给了对方五块钱,让她去镇上医院验血型——结果出来是o型血,和自己的A型、老陆的Ab型完全不匹配。
走出王家坳时,孙凤英再也忍不住,蹲在路边哭了起来,眼泪砸在黄土路上,瞬间就洇成了小坑。
第二个女孩家在黄沙镇东头,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
他们去的时候,女孩正在院子里劈柴,斧头抡得虎虎生风,额头上满是汗珠。
看到她的第一眼,孙凤英的心就沉了下去——不到二十岁的姑娘,脸上却刻着与年龄不符的沧桑,手上全是老茧,指关节因为常年劳作而变形。
“这孩子命苦,她哥要娶媳妇,家里的活全压在她身上了。”女孩的大队长叹着气说。
那天,孙凤英看着女孩沉默地劈柴、喂猪、做饭,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临走时,又塞了五块钱让她去验血。